整个通宵,黄燕萍都排在长队里。
2012年7月4日,日内瓦迎来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此时的欧洲核子中心(CERN)主礼堂外排着蜿蜒的长队。等候在此的,是来自各国的物理学家。
大门一开,他们克制着内心的冲动,以最安静、文明、有序的方式“抢占”着座位。
作为国际合作组里资历尚浅的成员,黄燕萍没想过要占一个更靠前的位置,进门看见后排有座位,便坐了下来。
上午9点,这里向全世界发出了一条重磅消息:大型强子对撞机的ATLAS(超导环场探测器)和CMS(紧凑缪子线圈)实验组,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
那一刻,在无形的粒子物理学术世界里,另一道大门也打开了,竞争同样安静、文明、扣人心弦。不同的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尝试寻找一个更靠前的座位。
荣耀
再谈起十年前的经历,黄燕萍依然很开心。当初,CERN礼堂里的荣耀,有一份属于她。
2012年5月,黄燕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博士后出站,又去了威斯康辛大学做博士后,并加入威斯康辛大学在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国际合作组。
LHC是躺在一条27公里环形隧道里的对撞机。黄燕萍参加的是基于LHC四大探测器之一的ATLAS实验。ATLAS在英文里有“地图册”之意。
这个探测器能测出对撞出的各种粒子的能量、寿命、电荷等诸多参数。根据这些参数,粒子物理学家就能判断撞出的是哪些粒子。也正因如此,它成为了寻找新粒子的“向导”和“地图”。
粒子物理领域还有一张更大的“地图”——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模型中有61种基本粒子。其中,60种基本粒子逐一被验证,只剩下一种毫无踪迹——为粒子提供质量的希格斯粒子。
黄燕萍怎么也没想到,她在ATLAS只工作了两个月,就成为了最早看到希格斯粒子迹象的“幸运者”之一。
和很多粒子物理学家一样,这件事让黄燕萍获得了继续研究希格斯粒子的信心。此后,她辗转于威斯康辛大学、CERN、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并最终在2016年回到中科院高能所。如今,成为特聘青年研究员的她带领着高能所ATLAS团队完成了希格斯粒子性质的最新联合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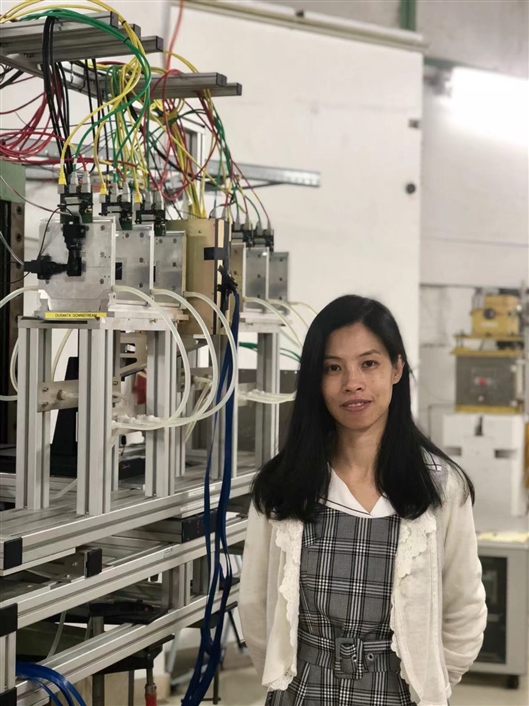
黄燕萍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暗潮
高能所研究员陈明水参与的是CMS实验。
相比ATLAS,CMS小很多,它通过更强磁场的线圈,可以更好地测量质子撞击后所产生的缪子。
2006年,还是博士研究生的陈明水和几位同学一起,第一次来到CMS,为的是把高能所为CMS研制的缪子探测器组装起来,并完成调试。
在希格斯粒子被发现前十年,高能所就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等团队负责人的领导下,在探测器建造、升级及网格计算方面做实质贡献。
对于陈明水来说,2012年就像一场粒子物理的盛宴。2012年3月8日,我国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开启了中微子物理发展的大门;几个月后,LHC发现希格斯粒子,又开启了希格斯粒子研究的大门。
盛宴开启后,陈明水能明显感到,粒子物理学界暗潮涌动,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陈明水的人生也跟着潮流一起涌动。他所在的高能所将ATLAS和CMS研究的长期核心科学目标凝练为希格斯粒子自相互作用研究。他自己也成长为高能所CMS组负责人,带领着高能所CMS组,完成了希格斯自耦合相关的最新联合分析结果。

2006年,陈明水(前排左一)参与高能所负责研制的阴极条室缪子探测器现场安装照片(受访者供图)
心结
除了发现希格斯粒子的两个主要探测器之外,LHC的其他探测器上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各大院所高校的粒子物理学家。
多年来,作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高原宁院士一直带领着中国团队参与LHC上另一个探测器——底夸克实验(LHCb)。
十年,他见证了中国团队在LHC国际合作组里的整体发展。
“到2021年,LHC中国组成员已超过500名。”高原宁告诉《中国科学报》。
这样的发展让高原宁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LHC中国组正在产生越来越多好的成果,担忧的是国际同行的目光。中国组的团队在扩大,成果在增加,但对LHC的实物贡献却没有太大变化。
从希格斯粒子被发现至今,LHC进行了升级改造和第二轮运行取数,刚刚开始了第三轮运行。这十年,中国组不是没有实物贡献,比方说,高能所带领的中国团队为LHC加速器升级项目成功研制了新型对撞区超导磁体,并主导了新型高颗粒度高时间分辨探测器项目的研制。但是,这些贡献与LHC的总投入相比,依然只占到1%。
1%,几乎成了参与LHC的中国科学家的心结。
“十年前是1%,十年后还是1%。在国际同行看来,我们就像是想‘摘桃子’,他们建好装置,我们直接进去就做物理分析、发表成果。”陈明水说。
不仅如此,没有投入,中国科学家也很难在一个庞大的国际合作体系中拥有话语权。“我们在探测器研制上的投入还很散,不是很有影响力。”高原宁坦言。
另一条路
除了参与国际合作之外,十年来,中国粒子物理学家还在尝试走另一条路——“以我为主”开展希格斯粒子研究的国际合作。
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打开了一道无形的大门,却没有解决所有困惑。新的疑问和好奇让全球粒子物理学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梦想:建一座能生产希格斯粒子的“工厂”,深入研究希格斯粒子的性质。
在提出“希格斯工厂”建设思路方面,中国粒子物理学家们走在国际前面。
2012年9月,以高能所所长、中科院院士王贻芳为代表的中国粒子物理学家,正式提出CEPC-SPPC设想,计划在中国建设一台周长100公里的、位于地下100多米处的环形对撞机希格斯工厂。
CEPC-SPPC的提出,曾改变许多中国粒子物理学家的人生。高能所研究员高杰就是其中之一。
高杰曾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终身研究员,自1992年起,他的研究工作一直聚焦在以发现和研究希格斯粒子为目标的未来正负直线对撞机设计和各种环形对撞机加速器关键物理问题上。2005年,高杰加入高能所。
在希格斯粒子宣布被发现之前,物理学家们推测,希格斯粒子可能具有很高的能量,因此,大家更倾向于关注能产生更高对撞能量的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2010年,高杰成为了亚洲国际直线对撞机(ILC)指导委员会主席,ILC的目标也是寻找和研究希格斯粒子。
可是,在物理学家确认希格斯粒子能量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之后,环形对撞机的优势也显现出来。CEPC-SPPC设想的提出,让高杰几乎将全部精力转向了环形对撞机的研究。

高杰的办公室里常年摆着一张国际研讨会的海报,海报上的“Higgs”(希格斯)一词十分醒目。(受访者供图)
坐席
2016年,CEPC-SPPC因为诺奖得主杨振宁等人的反对而引发社会关注。
就在国内科学与社会领域对“中国该不该建超级对撞机”争执不下时,2020年,CERN理事会全票通过《欧洲粒子物理2020战略》,提出了与CEPC-SPPC类似的计划,即基于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希格斯工厂”是“优先级最高的未来对撞机项目”,并期望建设能量尽可能高的质子对撞机。
及至此时,国际有了三个处于竞争状态的“希格斯工厂”计划——中国的CEPC-SPPC、日本积极争取建设的ILC,以及CERN规划的未来环形对撞机(FCCee)。
如今,高杰已是CEPC机构委员会副主席、CEPC环形加速器的负责人之一。他用“白热化”和“争先恐后”来形容十年来“希格斯工厂”、希格斯粒子研究的国际竞争态势。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2018年,CEPC完成了“概念设计报告”,目前已取得重要关键技术预研成果和技术瓶颈的突破,今年底将完成“技术设计报告”,随后进入“工程设计报告”阶段,为开工建设做准备。
作为CEPC的倡导者,王贻芳曾公开说:“中国的粒子物理如果做了CEPC,我就尽到我的责任了。这是从规划的角度来说。我可能看不到它的重大科学成果,也没机会在它上面做研究了。”
在争议声中,明知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在CEPC上做研究,他们还是坚持推动CEPC。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劲:下一次学术殿堂的大门打开时,中国要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占据一席之地。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