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任教是董若冰2024年的头等大事。这一年里,他的身份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副教授,转变为北京大学天文学系和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教授。
严格来说,截至1月份,他回国任职也才4个多月。《中国科学报》记者第一次跟董若冰联系的时间是2024年9月初,彼时他还要回加拿大处理一些搬家的“尾巴”——他在回国前把一些家当放在了当地的一个仓储。
自2008年从北大物理学院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国外辗转。2013年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亚利桑那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然后就在维多利亚大学执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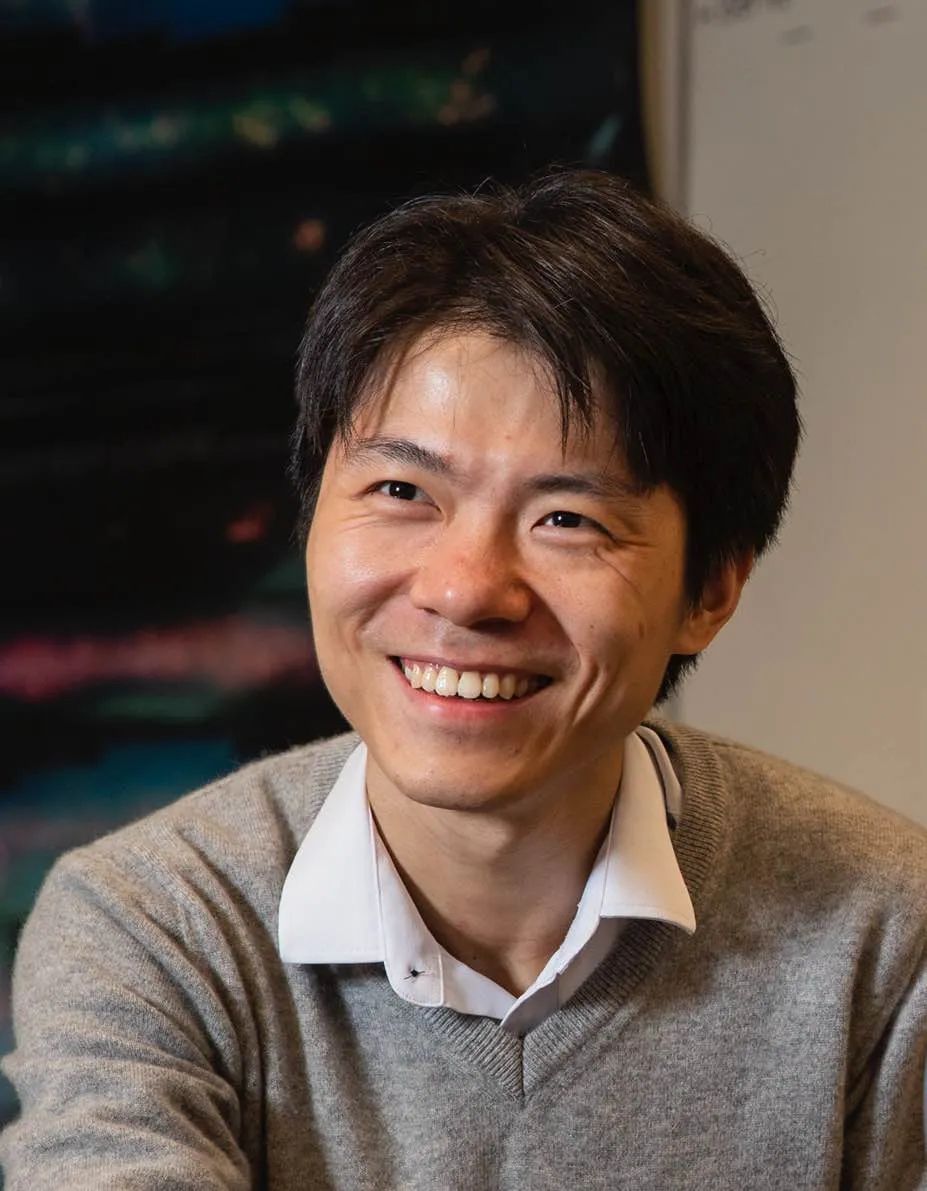
回国后,他的习惯变化不大。需要改变的,一是因为加拿大三相插头和中国的不一样,需要添置插座转换器;二是之前经常自己做饭,如今他每天去吃食堂。
岁末年初,他躺在床上思来想去,总觉得有点虚度。这一年做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是开会就是在写申请;不是答辩就是在办入职。不管怎样,他还是在这一年里窥到了国内科教界的面貌。
在维多利亚大学,董若冰的离职手续很简单,“就一封辞职信,那人签个字就行了”。那个人指的是系主任。
因为自己是从北大毕业的,加上之前多次回母校交流,北大对他的工作自然了解很多。这种情况下,回母校任教显得水到渠成。
董若冰研究的方向是系外行星如何诞生,属于行星科学领域。本来就小众的天文学的分支,再往下细分,还有太阳系内行星和系外行星。董若冰关注的是后者。之所以小众,很大原因是除了发表论文,天文学的研究不容易直接进行成果转化,因而无法吸引资本层面的投资。
董若冰在研究上采取了“观测-模拟-AI解读”三管齐下的策略:利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等最先进设备观测星周盘,捕捉行星形成的蛛丝马迹;同时,借助超级计算机模拟星周盘物理过程,并计划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加速数据解读和建模分析。
带学生这事儿,在国内和国外没什么区别。他还有两个加拿大学生,其中一个快毕业了,另一个还需要两三年,“我留了一笔钱继续‘养’着他们,毕竟要付学生工资”。董若冰平时跟他们远程沟通,再定期到加拿大跟他们交流,把他们带到毕业,也就善始善终了。
还有一个学生来自中国。当时董若冰给了这个学生三个选项:选项一是留在加拿大继续学习,可以获得远程的指导和讨论;选项二是转到北大继续读博;选项三就是拿着导师的推荐信去找其他教授再读博。
这个学生选择了第二条路。因为北大没有转学制度,他在加拿大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到北大跟着董若冰继续读博。
按照一些大学排行榜的排名来看,维多利亚大学远远比不上北大,貌似这个学生赚到了。但董若冰不这么认为。在加拿大没有国内这么卷,学生也没有北大学生那么要强,“谈到人生机遇,我们很难创造一个平行宇宙,去比较处于另外一种情况会怎么样”。
在北大,他再次回到了白手起家的状态。目前他有两个学生,除了那位跟着回国的学生,还招了一个新生。好在他们天文学家没有实验室的拖累,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完成课题组的迁移。
不过,留在加拿大的一个学生还是有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时差的关系,每当她有了研究想法,都不能及时与导师沟通。
“圈子”
抱着这个略带“功利”的目的,回国3个月里,他参加了6个会议。那段时间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路上。仅南京他就去了3次,因为恰巧有3个学术会议都在南京。
他很快发现,国内研究系外行星的同行太少了,不过寥寥数十人。这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申报项目的数量就能估算出来。
尽管北大对他没有论文考核要求,但董若冰还是有研究压力。毕竟他刚回来,需要证明自己,平时同事也会问他有什么突破性工作的计划。在某个基金申请动员会上,有学校领导提醒在座的教职工,不要总想着去发几篇小paper,而是要想着怎么做出突破性研究,怎么做出重磅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9月4日,董若冰团队发表了一篇《自然》论文,这也是他们课题组发表的第一篇《自然》论文。这篇论文对于行星形成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推进。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界一直以来有两个理论猜测。理论甲是经典理论,认为行星是从最初非常小的种子逐渐成长而来;理论乙则认为,如果星周盘具有引力不稳定性,巨型原行星就可以直接由引力不稳定性引发的巨大螺旋臂崩塌碎片形成。后者的前提是,星周盘的质量不能太小,个头至少要达到中心恒星的十分之一。
直接观测行星形成的难度极大。董若冰打了个比方,科学家只能看到无数个摇篮,但没办法识别其中的新生儿。
这就需要采取其它手段。就像通过看到飞机在天上拖曳的“尾迹云”来判断飞机存在,如果一个有质量的物体通过引力改变了周围物体的运动,就可以推测其存在。
基于此,董若冰和合作伙伴使用位于智利的由射电望远镜构成的天文干涉仪ALMA,在一颗位于御夫座的变星御夫座AB观测到了对理论乙有利的实质证据。
他们发现,观测到的动力学信号与模拟和解析模型的预测高度接近,并且星周盘的质量可能高达恒星质量的三分之一。
 董若冰在美国死亡谷
就在最近,天文学系二年级以上的博士生进行了一场年度考核,大概有50多个博士生参加。教师们也很积极地给每个人打分。这些博士生每人都需要作一个7分钟的报告,然后有8分钟的答辩时间。这个考核持续了两天。
这跟在加拿大不一样,维多利亚大学只是要求导师
委员会(由导师以及另外两个导师组成)每6个月到12个月跟研究生进行集体面谈,并无打分这么严格。
令董若冰印象最深的,是北大博士生的英文报告能力都不错。他也注意到,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答辩完以后,董若冰收到了一封群发邮件,其中有一份目前正在读第六年的博士生名单。大意是叮嘱导师们予以重视,希望确保这些延毕的博士生能够按时毕业。
董若冰之前的学生都按时毕业了。最近,他留在加拿大的一个博士生也收到了博士后的offer。也就是说,这个学生的毕业也几乎板上钉钉了。
天文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是不确定导师的,这些学生会去找各个教授聊天。当有人来找董若冰,并信誓旦旦称自己以后会做教授、走学术路线时,董若冰就会问对方:“你知道现在在北京做教授一年拿多少钱吗?”他认为,如果要严肃思考这个职业发展道路,这些信息挺重要的。
一些学生关心的,大都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如“你是干啥的”“你们课题组都折腾些啥”。
北大元培学院本科生宋禹辰告诉董若冰,他选择了物理专业,但还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问自己将来做什么。目前虽然自己学了量子力学,但是扭头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把四大力学攻下来了,而自己并没有坚定信念要做理论物理学家,不免心生焦虑。
董若冰丝毫没有犹豫,给出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评论:“起跑快,对跑完马拉松几乎是没有实际影响的。你们还早。”
就在2024年9月初,董若冰给物理学院的新生做了一个发言,差不多就是在回答宋禹辰这个疑问。
他回顾了自己的物理学生涯,提出:按照惯性、依据绩点“排队上车往前走”不应该是人生目的,人生应该有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可能性。因为总有一天,所有的车都将到站,“你总归要一个人看清方向,独自上路”。(这个故事详见《一位名校教授的人生自省:别让“排队上车”成为你的目标》,文中的主人公安山即董若冰)
二年级的宋禹辰当时读到董若冰这个发言,顿觉醍醐灌顶。“董老师这个讲话在物理学院是一股清流”,他立即转发到了朋友圈。
董若冰给宋禹辰讲了自己大一的一个故事。某次高数考试不理想,他去老师办公室查分,结果没查到。老师看到他很失落,就告诉他:“在北大,分数考高一点低一点真的不重要。”
那时的董若冰还不能理解这句话,他的同学也不能理解,一个好朋友甚至会因为考了89分而痛哭。
其实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董若冰最愿意拿出来讲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他想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用到天文学系领域中。因为大部分同行更注重拿到更新的数据,而不是用最新的技术,多数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人工智能技术。
这也是董若冰如此重视人工智能的原因,只有利用最新的工具,才能加速对观测数据的解读。他和自己最近招收的一个学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025年,他还要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一个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项目申请中。那是一个团队项目的申请,申报书至少要写数十页。
当被问及长远规划时,董若冰苦笑了一下。眼下有太多干不完的事情,每天就像救火,他根本无暇静心细想。
除了要撰写那个创新项目申报书,他还在筹备一个培训班。北大要邀请国外某位天文台负责人来讲解如何申请他们的望远镜时间,这无疑是天文学家最为看重的。那是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董若冰负责组织这些活动。
有一类活动是董若冰愿意花时间做的——他所在的研究所会邀请一些校友来给学生讲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学术圈和非学术圈。他邀请过自己本科同宿舍的下铺,如今从事金融业务。那次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从事量化交易的传奇校友舒琦,董若冰对舒琦的印象是“挺朴实”。(舒琦的故事详见《90后北大博士:毕业前已财富自由,给母校捐款超1000万》)
他想看看别人是如何拒绝“排队上车”的,也希望这些过来人的经验可以给正在北大读书的同学一些启示。
董若冰的社交圈子很简单。在加拿大的时候,虽然在维多利亚大学待了6年,但临走之际,有近一半的同事只是面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
他在北京有十来个本科同学,但一直都没有聚会过。本科下铺的好朋友一直在鼓动聚会,却一直凑不够人。
什么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董若冰的答案和去年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的如出一辙——当然还是好奇心。他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董若冰在美国死亡谷
就在最近,天文学系二年级以上的博士生进行了一场年度考核,大概有50多个博士生参加。教师们也很积极地给每个人打分。这些博士生每人都需要作一个7分钟的报告,然后有8分钟的答辩时间。这个考核持续了两天。
这跟在加拿大不一样,维多利亚大学只是要求导师
委员会(由导师以及另外两个导师组成)每6个月到12个月跟研究生进行集体面谈,并无打分这么严格。
令董若冰印象最深的,是北大博士生的英文报告能力都不错。他也注意到,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答辩完以后,董若冰收到了一封群发邮件,其中有一份目前正在读第六年的博士生名单。大意是叮嘱导师们予以重视,希望确保这些延毕的博士生能够按时毕业。
董若冰之前的学生都按时毕业了。最近,他留在加拿大的一个博士生也收到了博士后的offer。也就是说,这个学生的毕业也几乎板上钉钉了。
天文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是不确定导师的,这些学生会去找各个教授聊天。当有人来找董若冰,并信誓旦旦称自己以后会做教授、走学术路线时,董若冰就会问对方:“你知道现在在北京做教授一年拿多少钱吗?”他认为,如果要严肃思考这个职业发展道路,这些信息挺重要的。
一些学生关心的,大都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如“你是干啥的”“你们课题组都折腾些啥”。
北大元培学院本科生宋禹辰告诉董若冰,他选择了物理专业,但还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问自己将来做什么。目前虽然自己学了量子力学,但是扭头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把四大力学攻下来了,而自己并没有坚定信念要做理论物理学家,不免心生焦虑。
董若冰丝毫没有犹豫,给出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评论:“起跑快,对跑完马拉松几乎是没有实际影响的。你们还早。”
就在2024年9月初,董若冰给物理学院的新生做了一个发言,差不多就是在回答宋禹辰这个疑问。
他回顾了自己的物理学生涯,提出:按照惯性、依据绩点“排队上车往前走”不应该是人生目的,人生应该有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可能性。因为总有一天,所有的车都将到站,“你总归要一个人看清方向,独自上路”。(这个故事详见《一位名校教授的人生自省:别让“排队上车”成为你的目标》,文中的主人公安山即董若冰)
二年级的宋禹辰当时读到董若冰这个发言,顿觉醍醐灌顶。“董老师这个讲话在物理学院是一股清流”,他立即转发到了朋友圈。
董若冰给宋禹辰讲了自己大一的一个故事。某次高数考试不理想,他去老师办公室查分,结果没查到。老师看到他很失落,就告诉他:“在北大,分数考高一点低一点真的不重要。”
那时的董若冰还不能理解这句话,他的同学也不能理解,一个好朋友甚至会因为考了89分而痛哭。
其实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董若冰最愿意拿出来讲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他想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用到天文学系领域中。因为大部分同行更注重拿到更新的数据,而不是用最新的技术,多数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人工智能技术。
这也是董若冰如此重视人工智能的原因,只有利用最新的工具,才能加速对观测数据的解读。他和自己最近招收的一个学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025年,他还要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一个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项目申请中。那是一个团队项目的申请,申报书至少要写数十页。
当被问及长远规划时,董若冰苦笑了一下。眼下有太多干不完的事情,每天就像救火,他根本无暇静心细想。
除了要撰写那个创新项目申报书,他还在筹备一个培训班。北大要邀请国外某位天文台负责人来讲解如何申请他们的望远镜时间,这无疑是天文学家最为看重的。那是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董若冰负责组织这些活动。
有一类活动是董若冰愿意花时间做的——他所在的研究所会邀请一些校友来给学生讲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学术圈和非学术圈。他邀请过自己本科同宿舍的下铺,如今从事金融业务。那次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从事量化交易的传奇校友舒琦,董若冰对舒琦的印象是“挺朴实”。(舒琦的故事详见《90后北大博士:毕业前已财富自由,给母校捐款超1000万》)
他想看看别人是如何拒绝“排队上车”的,也希望这些过来人的经验可以给正在北大读书的同学一些启示。
董若冰的社交圈子很简单。在加拿大的时候,虽然在维多利亚大学待了6年,但临走之际,有近一半的同事只是面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
他在北京有十来个本科同学,但一直都没有聚会过。本科下铺的好朋友一直在鼓动聚会,却一直凑不够人。
什么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董若冰的答案和去年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的如出一辙——当然还是好奇心。他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