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通进(左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与罗尔斯顿(左三)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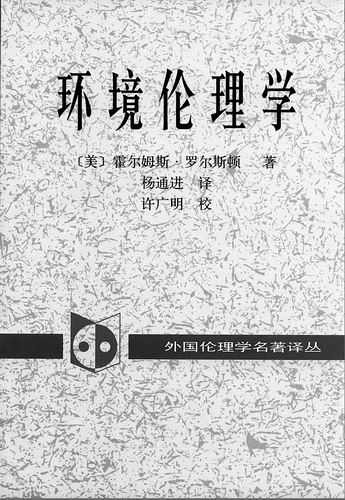
《环境伦理学》封面。受访者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
受访者:杨通进
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环境伦理学》中文版译者。曾于2001年9月至2002年11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师从罗尔斯顿。
《中国科学报》:作为与罗尔斯顿交往密切的学者,你眼中的罗尔斯顿是怎样的人?他的教学方式或学术研究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特点?
杨通进:罗尔斯顿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有影响力、也最为著名的学者。他于1975年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伦理学》上的长篇学术论文《生态伦理是否存在?》,确立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1979年,国际环境伦理学最重要的学术平台《环境伦理学》杂志在他的帮助下创刊。1990年他创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2003年,他建议并领导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个环境伦理学国际项目“环境伦理学与国际政策”。他的《哲学走向荒野》和《环境伦理学》是国际环境伦理学界引用最多的两本著作。
罗尔斯顿还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学术使命感的学者,他宣讲环境伦理学的足迹遍及七大洲。他曾于1991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并给我国学者带来了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新的学术资料,打通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界与国际环境伦理学界的学术通道;此后,他又多次来华讲学,为推动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尔斯顿不仅治学严谨,还尊重自然、身体力行地爱护环境,这不仅是他倡导的一种价值观,更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访学那时,他已年近七旬,家距离学校有3公里路程,只要不刮风下雨,他都骑自行车到校上课和办公。每逢假期,他都到野外聆听大地的声音,感悟自然的神奇。他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要求严格,阅读任务繁重。但是,课堂生动有趣,师生在学术争论中不断迸发思想火花。
《中国科学报》:2000年,《哲学走向荒野》和《环境伦理学》的中译本分别被列入“绿色经典文库”和“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在国内出版,彼时国内关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学术讨论氛围如何?这两本著作在学术界有什么样的反响?
杨通进: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由于资料缺乏,一直进展缓慢。这两本译著以及1999年出版的罗德里克·纳什所著的《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为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料和思想灵感。
1994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开拓者余谋昌先生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学术大讨论。在那场争论中,绝大多数人仅止于从工具价值的角度理解环境保护的意义。罗尔斯顿的上述两本著作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揭示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以及大自然对于人类精神生活与终极关怀的重要意义,使越来越多的学者理解并接受了余先生所指明的理论方向。
《中国科学报》:有学者认为罗尔斯顿的理论存在“实践局限性”“主体泛化”等不足,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杨通进:任何一位学者自身都存在局限性。罗尔斯顿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上述两种批评值得商榷。首先,不能笼统地说,罗尔斯顿的理论存在“实践局限性”,因为他的《环境伦理学》一书专门用三章篇幅讨论如何在公共政策、商业活动与个人生活中践行环境伦理的问题。其次,“主体泛化”的批评也需要具体分析。罗尔斯顿把价值主体的范围从人扩展到了人之外的动物、植物和地球生态系统,这主要是为了给人对动物、植物和地球生态系统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提供一个超出工具价值的伦理基础,这涉及人的终极关怀问题。
在我看来,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的主要局限可能是,他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之根源及其化解之道的理解或许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与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的环境伦理学可能存在“国际政治盲点”。
《中国科学报》:罗尔斯顿曾提到,要创立一门“属于中国的环境伦理学”,你认为我们现在实现这一目标了吗?当前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杨通进:罗尔斯顿的一个令人敬佩的学术眼光就是,他充分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体性”,并前瞻预见到崛起的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他在《环境伦理学》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明确提出“除非(且直到)中国确立了某种环境伦理学,否则,世界上不会有地球伦理学,也不会有人类与地球家园的和谐相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点。
与罗尔斯顿一样,我国学者也意识到创建环境伦理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经过近40年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学派仍处于“进行时”。一个学派的形成和诞生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一个可喜的信号是,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展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我国的环境伦理学也在环境保护实践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标识性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为环境伦理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观念基础,并提供了价值取向。
展望未来,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需要加快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哲学基础与伦理规范的研究,深化对“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阐释,进一步强化对气候伦理、实验动物伦理、能源伦理、农业伦理、林业伦理等新兴议题的跨学科研究。只有这样,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学派才能最终走向成熟,成为全球环境伦理学大花园中的绚丽花朵。
《中国科学报》:从1975年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到现在,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已历经五十个春秋。如今,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具有哪些划时代价值?当前,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他的理论如何回应“人类世”的伦理困境?
杨通进: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及其环境哲学思想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为我们理解和思考现代性的困境之一“自然的祛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自然的祛魅”这一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自然的精神价值被工具理性和机械自然观侵蚀殆尽,自然蜕变成了僵死的原料仓和资源库,人也蜕变成了只受“利己主义动机”驱使的自私的物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意义联系被完全斩断;人变成了在茫茫宇宙中无端漂浮的浮萍。第二,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驱使下,传统的工业文明在不断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的同时,破坏了人类文明的自然根基。
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人类需要纠正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认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在文明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同时,人类需要认可并接受人对自然的伦理义务,用伦理规范约束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世”的伦理困境是工业化与不公正的全球秩序高度合谋的产物。面对这一新兴挑战,包括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在内的大多数伦理学理论都没能提供完整的方案。这主要缘于大多数伦理学理论都存在“国际政治盲点”。导致这种国际政治盲点的罪魁祸首是尚未被理性启蒙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传统。
只有发展出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即消除了狭隘人类中心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传统的文明形态,人类才能成功应对“人类世”的伦理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提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型文明形态的到来指明了方向。
《中国科学报》 (2025-02-21 第3版 读书)